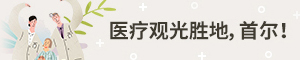▲从《少年巴比伦》到《慈悲》,您觉得您作品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慢慢地学会了写所有题材的小说。以前感觉只会写90年代少年题材,十多年过去了,虽然这个时间对于作家而言并不长,但在完成七、八部长篇小说之后,尤其是今年刚刚写完了一部将于年底出版的四十万字长篇小说后,感觉在技术上会提高很多,比如在题材的把控上。成为职业作家以后,确实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去放宽眼界,看现实的世界、看历史的世界以及文学史所表达的世界。你会产生一些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比如与前一代作家的比较,或者去和整个亚洲范围内的文学进行比较。简而言之,小说会写得更好一些,眼界会更宽一些。这是职业作家的优势。当然,职业作家也会有他的弱势,有些人有的时候可能被环境、 商业、政治所左右,简单地讲,这也是作家自我的减弱。
▲您之前的作品会经常出现90年代、工业城市以及偏向底层出身的人物形象,未来您的小说中还会一直坚持使用这样的设置吗?
对我而言,我不是故意要写90年代的故事,那确实是我20多岁经历的事情,在我的角度那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社会关系可能不是很复杂,但是他介入社会的程度一定是最高的,甚至他总会怀有一些不满。他的感受和中年及老年会不一样。所以我会选择写90年代。90年代也是中国巨变的年代,但是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是奔着巨变去的,只是那个时代的感受会比较深一些。这些东西会成为作家最先使用的素材,然后也会慢慢发现这里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需要去写。我现在感觉我已经把90年代故事讲完了,以后也许会更多地选择其他题材。
对于城市这个问题,中国的农民人口比重其实很高。在对一个城市进行界定的时候,当以人口来计算时,它是一座大城市;但是以经济来计算时,它又是个小地方。这个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小说家、电影导演一直在试着去阐释的一个问题,人口众多,生态复杂,但是经济不是很发达。不过这些年下来,我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很大变化,慢慢我们会发现,这是需要重新去认知的一个东西。对我而言,这两年去写农村贫困的小说已经不太好写了。要提笔去写,你得先问当地的精准扶贫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现实不能瞎写,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就是非常不满足于只写一个地方。这部小说中,我写了二十多个城市,从北方写到了南方,这样就把小说整个时间线和空间范围扩大。我不太满足于给自己贴上南方作家还是北方作家这样的标签。中国很大,南北作家本身自带的风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背后也隐含着历史和文化。这也是我们与日韩作家所不一样的地方。
▲《慈悲》这部作品2017年在韩国正式出版,请您聊一聊这本韩译本出版背后的故事。
《慈悲》在韩国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翻译输出项目中的一部分。当时除了韩语,还翻译了阿拉伯语、伊朗语等语言。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小说会往东翻译。被翻译为韩语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在中国往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东亚文化圈,我们之间会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的作品能翻译到韩国来、被韩国的读者看到,我真的很感动。我总会这样认为,西方读者在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可能会感受不到。他的感受和东亚文化圈是不一样的。就像我看韩国的电影就不会问为什么会这样,而是说我们也是这样的。它确实有共同点,我们会本能地去理解。韩译本的翻译工作算是顺利,这期间也没有与韩国翻译家联系。这可能也与这本小说句法较为简单有关。之前的小说可能会更复杂一些,使用大量的俚语,但这本就会相对简洁一些。
▲您现在写小说时会特别注意到语言的简洁性吗?
我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可能会往反方向走。因为写一个小说如果只是贪图简洁,考虑翻译方便的话,对小说家来讲会产生巨大的问题。你的句法、你所表达的东西会减损。我写《慈悲》之所以选择较为简单的句法,是因为它写了很多我出生之前的历史。我对既往的历史其实并没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使用,我也不愿在家庭生活的描写中填充太多细节和修辞,以至于它变得很冗长,所以就使用了这样的“方案”。但我不会在所有小说中都这样去处理。我会去估算一个长篇小说用什么合适的方式来完成,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会追求它的复杂度,让他的语言能够和节奏变化能更多一些。如果只考虑翻译的简洁性,语言的影响会非常微妙,进而导致你的观念走形,产生主题先行。
▲您对韩国文学有哪些了解?刚刚提到您喜欢看韩国电影,有哪些喜欢的作品吗?
今年我注意到中国有文章大量地去介绍韩国女性作家,这反映出中韩社会同时出现一些在女权问题上的诉求。从这样的诉求中就会发现中国的读者也会去关注韩国的女作家和她们的表达,并对她们进行很高的评价。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对韩国作家的高度赞扬,一方面也是中国女性一些需求的出现。中国近年来反映女性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其实不算多,这次从韩国回去之后,也打算好好看一下韩国作家的作品。其实读韩国作品还存在一个翻译问题,如果有好的译者,作品会更容易接触。同时,韩国的文学可能还缺少一个契机,比如像拉美文学运动,它一下子就成为世界主流的一部分,也许未来韩国文学也会慢慢成为亚洲文学的主流。
谈到韩国电影,我比较喜欢奉俊昊导演的作品以及金基德导演早期的一些作品。《杀人回忆》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而宋康昊这样的演员也在大陆很受欢迎。
▲您在写小说时,是否有一些想要传达的内容?
我有时会愿意写我自己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但是它的出发点完全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而是个人的,甚至它可能是很浅薄的、对时间流逝的一种伤感。但是在写的过程中,就会碰触到一个更大的东西,看到原来我们过去那一代的年轻人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举个有意思的例子,现在中国已经很强大了,所以这一代年轻人会感到很骄傲。但这与我青年时代反差太大了,青年时代我看到亚洲四小龙是有自卑感的,这是很奇异的东西。但是当你注意到这个的时候,你瞬间会感受到这里面包含着历史和政治。这是一体化的。
我更愿意从个人角度去阐述一些东西,如果纯从历史角度,这是社会学家要做得事情。在我看来小说是带有诗意的东西。虽然中国会更多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小说需要带有诗学上的虚无主义,这与历史虚无主义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也很希望去尝试创作更多时间点和时间段的作品。我认为,在45岁前后会变得不一样。45岁之前我愿意从自己的体验去写;而45岁之后,我会更多从思考、文本和技术等方面去完成我的长篇小说作品。

作家路内 【摄影 记者 李佳星】